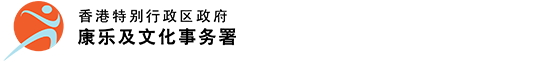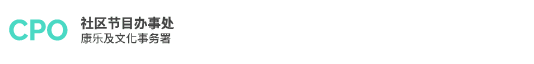第一次见面时,她拿着一个帆布手提袋,上面是由不同针法编织而成的花纹,细看才会发现,那是蓝屋故事馆的斜孭袋,但她用针线在上面绣上了不同图案,故事馆的楼顶绣了树叶,窗口有金鱼,繁花铺满楼瓦,中间有一道花桥贯穿蓝屋的横梁。
「我自己绣的,仅此一个。」May姐自豪地说。
May姐的名字并不陌生,不论是关于她先前参与利东街或皇后码头的经历,还是后来到不同的重建区支援各区街坊,你总会看到一个气势磅礴、毫不畏惧的娇小身影,她像是「停不下来」,以她烈火般的气魄却又不失圆滑的言辞──故有「蛊惑女」之称──来诉说湾仔的故事。我称她为烈女,把一生过得轰轰烈烈,而直到现在的余温还是暖烘烘的。
住在湾仔超过六十年,曾经于利东街摆手作饰物档口,那是她的风骚时光,朝早摆档,然后下午二时收工,就算有客人也拒诸千里,十分「招积」。May姐说,越是关心社会就越充满挫败感,反而最开心的,是在利东街卖手作饰物时的日常,包括每个街坊的一句早晨,和客人对饰物的称赞。
「他们将我的生活和商业营运模式,一次过打烂了。」
多次在报章、电台和旅游节目等去讲解街道的前生,透过往事去提醒城市的人,我们曾经失去过什么、正在失去什么、将会继续失去什么,May姐说,直到现在,她都不会听《禧帖街》这首歌:「听了,就等于承认她已成过去。」独自一人的时候,都不会再走到新的利东街去,曾经有旅游节目要她介绍利东街的前世今生,她就只说前世,今生只字不提,有风骨之余,难免替她感到凄凉,但她却说:
「唔行利东街,就行春园街,人总要向前行。」
在这句潜藏极强大人生哲理的金句背后,我仿佛看到May姐,用着她独具匠心的不同针步,绕过无数零散碎布,在生命里每一寸无法确定的咫尺之间勇敢地落针──烈女的针步,针针有力而不失柔劲,回过头来,她已经一步步缝纫出自己的故事:「一匹布咁长」。
道别时,我终于按捺不住,问May姐帆布袋上的绣法,她耐心地指着每个图案,这里跳了针、那个针步是回针、贯穿蓝屋横梁的花桥用了法国结针法等⋯⋯越讲越兴奋,眼神和刚才说重建项目时截然不同。
习惯了义愤填膺的人,原来都可以有这样的神情,毕竟投身于社会的人,通常只会被记住事迹,但其实他们往往比起其所承载的理想更广阔、更立体、更接近一个人。我庆幸可以认识到访问以外的May姐,因为每次和她的对谈──甚至只是旁听,心里仿佛就可以燃点起一些什么似的,她像火,可以燎原又可以取暖,必要时,为荒凉照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