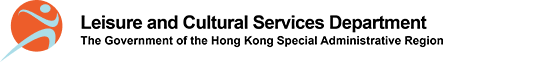*Chinese version only
《烈女針法》
第一次見面時,她拿着一個帆布手提袋,上面是由不同針法編織而成的花紋,細看才會發現,那是藍屋故事館的斜孭袋,但她用針線在上面繡上了不同圖案,故事館的樓頂繡了樹葉,窗口有金魚,繁花鋪滿樓瓦,中間有一道花橋貫穿藍屋的橫樑。
「我自己繡的,僅此一個。」May姐自豪地說。
May姐的名字並不陌生,不論是關於她先前參與利東街或皇后碼頭的經歷,還是後來到不同的重建區支援各區街坊,你總會看到一個氣勢磅礴、毫不畏懼的嬌小身影,她像是「停不下來」,以她烈火般的氣魄卻又不失圓滑的言辭──故有「蠱惑女」之稱──來訴說灣仔的故事。我稱她為烈女,把一生過得轟轟烈烈,而直到現在的餘溫還是暖烘烘的。
住在灣仔超過六十年,曾經於利東街擺手作飾物檔口,那是她的風騷時光,朝早擺檔,然後下午二時收工,就算有客人也拒諸千里,十分「招積」。May姐說,越是關心社會就越充滿挫敗感,反而最開心的,是在利東街賣手作飾物時的日常,包括每個街坊的一句早晨,和客人對飾物的稱讚。
「他們將我的生活和商業營運模式,一次過打爛了。」
多次在報章、電台和旅遊節目等去講解街道的前生,透過往事去提醒城市的人,我們曾經失去過甚麼、正在失去甚麼、將會繼續失去甚麼,May姐說,直到現在,她都不會聽《囍帖街》這首歌:「聽了,就等於承認她已成過去。」獨自一人的時候,都不會再走到新的利東街去,曾經有旅遊節目要她介紹利東街的前世今生,她就只說前世,今生隻字不提,有風骨之餘,難免替她感到淒涼,但她卻說:
「唔行利東街,就行春園街,人總要向前行。」
在這句潛藏極強大人生哲理的金句背後,我彷彿看到May姐,用着她獨具匠心的不同針步,繞過無數零散碎布,在生命裏每一寸無法確定的咫尺之間勇敢地落針──烈女的針步,針針有力而不失柔勁,回過頭來,她已經一步步縫紉出自己的故事:「一匹布咁長」。
道別時,我終於按捺不住,問May姐帆布袋上的繡法,她耐心地指着每個圖案,這裏跳了針、那個針步是迴針、貫穿藍屋橫樑的花橋用了法國結針法等⋯⋯越講越興奮,眼神和剛才說重建項目時截然不同。
習慣了義憤填膺的人,原來都可以有這樣的神情,畢竟投身於社會的人,通常只會被記住事蹟,但其實他們往往比起其所承載的理想更廣闊、更立體、更接近一個人。我慶幸可以認識到訪問以外的May姐,因為每次和她的對談──甚至只是旁聽,心裏彷彿就可以燃點起一些甚麼似的,她像火,可以燎原又可以取暖,必要時,為荒涼照明。